目录
快速导航-
编辑部札记 | 黑虎虾与路径依赖
编辑部札记 | 黑虎虾与路径依赖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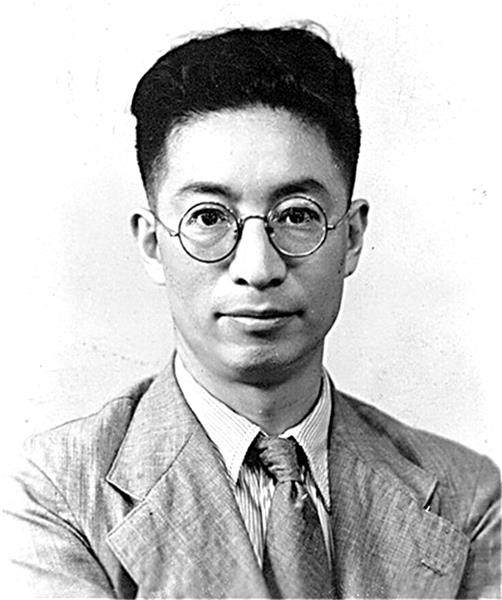
| 郑振铎与新文学社团、刊物、作家群
| 郑振铎与新文学社团、刊物、作家群
-
| 重返通灵之所
| 重返通灵之所
-

| 重写初民世界的历史
| 重写初民世界的历史
-

| 古典今用
| 古典今用
-
| 说张元幹《贺新郎·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》
| 说张元幹《贺新郎·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》
-

| 梅川书舍札记(十一)
| 梅川书舍札记(十一)
-

| 旧体诗的回马枪
| 旧体诗的回马枪
-

| 图形·画影·画影图形
| 图形·画影·画影图形
-
| 金字塔的底部
| 金字塔的底部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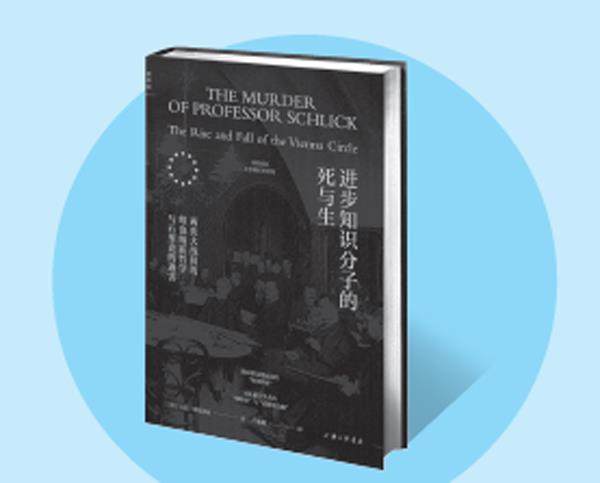
书间道 | 维也纳的璀璨时光
书间道 | 维也纳的璀璨时光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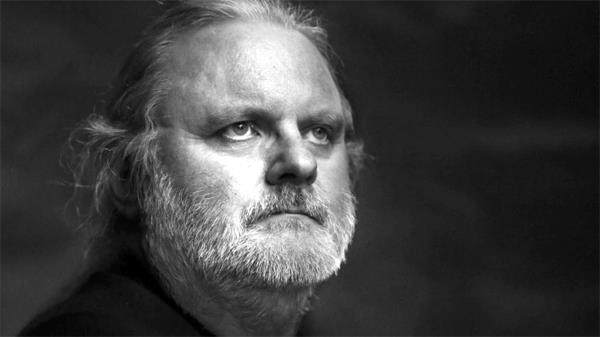
书间道 | 《三部曲》:现在我们驶入生活
书间道 | 《三部曲》:现在我们驶入生活
-

书间道 | “涂鸦社”的格列佛
书间道 | “涂鸦社”的格列佛
-
书间道 | 永远这只眼
书间道 | 永远这只眼
-

书间道 | 情感之泉涌起之后
书间道 | 情感之泉涌起之后
-
书间道 | 雪崩于无声之时
书间道 | 雪崩于无声之时
-

书间道 | 甘丹·梅亚苏的另一种“虚构”
书间道 | 甘丹·梅亚苏的另一种“虚构”
-

书间道 | 宝树园藏书闲话
书间道 | 宝树园藏书闲话
-

书间道 | 李霖灿:观雪看画
书间道 | 李霖灿:观雪看画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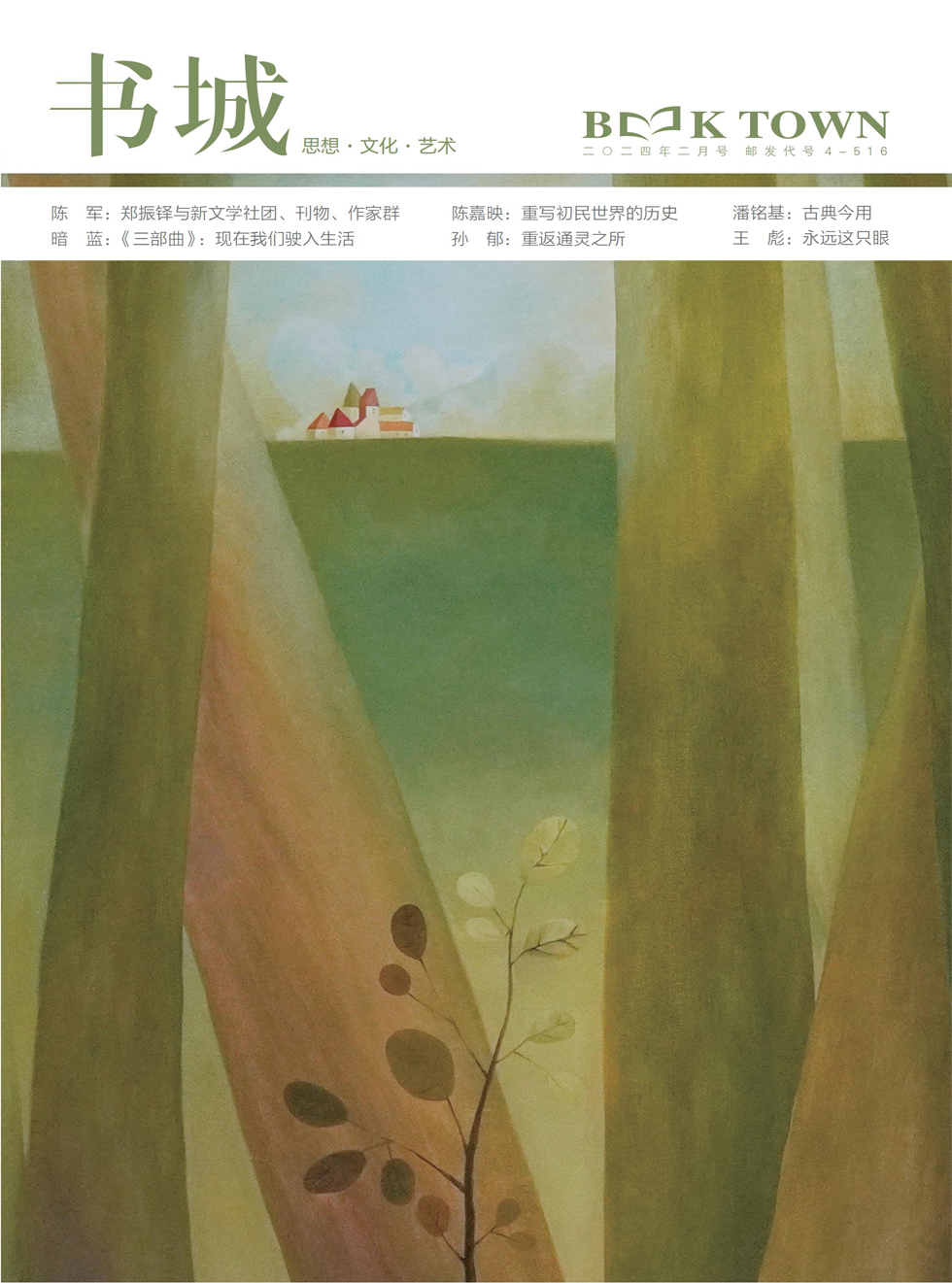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 登录
登录